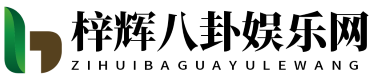- 活动公告
2015年6月20日晚上6点50-8点50,将在双城咖啡馆(北京市东城区 方家胡同 46号院)举办《青年电影手册——华语同志电影20年》读者分享会,届时主编程青松先生将和读者朋友们分享关于华语同志电影的故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蝴蝶》梦作者:田原

我和麦婉欣的故事似乎被说了许多次,再重复实属多余,不过我每次想到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总会禁不住自己笑一笑。汉语中有许多词虽然都快被用烂,但仔细推敲又会觉得微妙而脱俗,比如说‘一见如故’,这也许就是我和麦婉欣第一次见面的感觉。我们似乎很久以前就认识,而且相互之间有种微妙的信任。而信任恰好是演员和导演之间最需要的。
那时的我才刚刚高中毕业,虽看过许多电影,却从未真正接触过拍摄,我只有满脑子的想法,和实际平行。那次麦婉欣拿数码相机对我拍了一通,跟我用香港普通话聊天许多,现在回忆起来我只记得她问我:“你真的愿意拍电影吗?经常需要重复做许多次,是很辛苦很乏味的。”我想那时我还完全不懂她所指的辛苦和乏味,傻乎乎地说:“没问题啊!”
那次见面之后,我送给麦婉欣一本我的《斑马森林》,她在飞机上一口气就读完了,然后问我是否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片段用到《蝴蝶》中。当然没问题,我甚至愿意去写更多。于是,那个闷热的夏天里,我对着破旧的电脑,敲出了许多行字。我边看《蝴蝶》的剧本边去想象会是怎样的画面,想象两个女人之间的爱和遗憾。所以,我想到,如果一只拖鞋掉到楼下,另一只也一定应该跟随。
演员:田原
我对于《蝴蝶》的理解是:成全了一种遗憾,那么遗憾就成了美好。美好并不一定要是顺应他人的意志,或者符合所谓‘美好’的标准。
然而,从思想上的理解走到行动上的表现,是一个坎坷的过程。
又过来一年多,正式的拍摄终于要开始了。我请了几天假,懵懂着就去了香港,还没有睡醒便被拉去了片场。第一场戏就是在超市,阿蝶发现小叶偷吃东西被抓。那是我和阿蝶见面的第一场戏,是我第一次出现,理应是至关重要的一场。但我确是晕晕乎乎地演了下来,根本不知道机器在哪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演戏的节奏。我记得导演让我大口地吃饼干,好似很饿,我就非常实在地不断在吃,拍完那部分的时候已经被饼干撑满,自己偷偷去厕所吐了一阵。
拍到第二天,我开始有些紧张,因为很多拍摄的基本规则都不懂,我总害怕拖延大家的时间,候场的时候也是愣愣地看着大家忙来忙去,突然有些迷失。有时我会突然心里一沉,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究竟要做什么。经常拍到黑白颠倒,我会回到酒店看窗外的大海,有时傻乎乎的海鸟会撞到玻璃上,像我一样,没有定位还不愿意看清路。
这种低落一直持续到酒吧的拍摄,那里是片中小叶工作的地方,我换上了夹克和牛仔裤,抱起了吉他,突然又回到了正面的能量中。这时音响中传来了she的声音,这时我拿起吉他终于会演戏了。那一刻,我突然有点儿小小的觉悟,演戏是一个弄假成真的过程,要化忙碌的工作人员和刺眼的灯光为无形,在虚假的环境中去制造真的情感,要身心投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天之后,我才有真正是小叶的感觉,那个最正式的‘我’终于被瓦解了,开始投入角色。拍完的那天,我觉得生命突然变浓稠了许多,在短短的十多天拍摄中,我体会到了比过去18年还要多的情感起伏。
记得麦婉欣也曾经跟我说过,有点儿担心les群体看完我们拍的电影后是否能够接受,毕竟我们并非她们中一员,是否能够做到真诚和真实?
有几场重要的戏都是在小叶家中,剧组找到了位于湾仔的一栋老楼,装扮得活生生,到了那个场景,大家都非常有归属感。没想到,到真正拍亲密戏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儿紧张。Josie是一个直率、可爱的人,拍摄的时候也处处照顾我,所以后来让大家都面红的戏,我们拍起来其实很轻松。
不知不觉,一部戏就拍完了,像是一个缓缓醒来的梦,一部分梦的触角延续到了现实中。
拍完之后,我又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继续上学、考试、思考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等等。得知入围金像奖是又一年之后了,得知提名之后我被飞去香港拍了一次宣传图片。记得那时刚下飞机,被塞进了蹩脚的白色礼服中,拍得奇奇怪怪,我想我是肯定不会得奖的,所以拍摄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那天颁奖典礼我没有去,连新闻也没有听,最后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得奖了。据说当时台上冷场许久,因为制片公司也没有想到我会得奖,愣了半天才走上台去接过奖杯。
一切现在看起来真是有趣。

之后我又参演了许多电影,可以说是一路被动地去接受,有时甚至觉得丧失了自己。直到2011年,我才感面对那个内心的自己,她说她并不喜欢被人操控,也不愿意把一切都弄假成真。这时我又想起在酒吧拍的那场戏,突然明白那不完全是‘弄假成真’,而是将真实的情感在虚假的环境中还原成真实。
很多道理,都是洋葱,你拨开一层就以为明了,其实还有很多层要拨。
几年前,在一个club,我去洗手间,突然有个女孩激动地看着我,走上来握住了我的手。我愣了,直到她说她和她女朋友是受到《蝴蝶》的鼓励而继续下去的。这些年中,也不断会有人再给我提起《蝴蝶》给她们的希望和鼓励。是啊,《蝴蝶》中虽然有悲伤和矛盾,但结尾是温暖而开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只不过当你的选择和主流有偏差时,你需要付出更多来维护自己的选择。
2011年开始,我尝试自己去导演,因为我不希望再被动地被使用,去传达我并不欣赏和赞同的价值观和情感,我更想自己去创造,虽然这样很辛苦。我开始有一个信念:把真实的感情在搭建出的环境中还原成真实。这个信念,其实在《蝴蝶》之时便已萌芽。
该文章摘自《青年电影手册——华语同志电影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