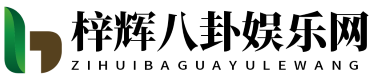- 文/赤道蚂蚁
无边的黑夜,是一张网,在每天睡觉的时候,噪杂的梦,却辜负了舒适的床.萦绕于午夜子时空洞的画面,有时会穿透时光的暗影,诉说着千山暮雪那片言不由衷的一往情深。我时常会因为黑夜的漫长和黎明的短暂,会突然想起斑驳而又绵延的爱与哀愁,不可折中的,是我翻动经年旧账的无奈,眨眼凌乱的,还是那双写满柔情的寂寞双眸。这些情绪,注定就是上古年代的凤凰春,它繁盛了一株稻秧的暮雪残冬,也叫醒了万顷紫薇的去意无留。

深深爱过一个人后,这些年,我已经忘记了再如何去爱。生活太过安静,声色佳期,恍若上一场梦境迷踪。我躲在一个个暗无天日的黑夜里,抒情,或是泄愤。星月集合起来,开始怄气,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尽头,唯有伪装,扮狼又扮虎,装神再弄鬼。
我恨透了这个催促自己去装逼而又犯贱的尴尬岁月,一片被扯裂的树林外,在阴森的一间房里,孤独和绝望被塞进凌乱的后花园里,深红浅白、长枪短炮,在偶尔泛起雾霾的清晨,时常牵引着的野猫、发疯的土狗,还有生病的斑鸠,它们似是朋友,又好像敌人,容不得每一次用以睡眠而兑换的躲避。于是,我总是自说自话地写着一些杂乱的文字,自己看不懂,别人读不懂,絮语如旧,感慨却刺穿了深埋于此的悲悯情绪。
在书写的案头上,我始终是一个罪人。寂寞成文,这一腔怨气,终是划破了一眠不醒的夜空,也炸裂了百年不落的黄日。
我是谁?我是一只潜行凤凰春里的妖狐。
前世,我祸害过曾经千娇百媚的后宫之妾。而今,注定要做回那个隔岸啼血的孤苦君王。
三年,清浅一笑。我魅惑了只身一人的漫漫长夜。随后,每一个森严的晚空里,我以为只要穿越壮阔湛蓝的汪洋,就足以召回叠浪拍岸的灿烂天明。直到五更来袭,睁眼回望的瞬间,瘫软不起的,仅仅一场宿醉而已。
我终于开始相信了别人的话,我写的文字,没人能够看得懂。掺着无序的节奏,一帧帧朝前循环,又一帧帧向后回放。我躲在原地,听海哭的声音,也听一只妖狐的彻夜愁怨。
装逼,是一件不能自已的事情。有时候,偶尔想起就不联络的一个朋友,约好午后喝茶,半夜喝酒,起初我喜欢你是静静的,到了最后,却被折腾的杯盘狼藉。没有缘由的翻脸,再毫无征兆的和好如初,这般往返,周而复始,对镜凝望,熟悉着陌生的,不是那个远去的时空,而是近在咫尺的这张脸。
的确。你除了歇斯底里的装逼,还能做些什么?
原来,每一个走向寂寞深处的人,都渴望用生活的倦意,去兑换一餐后的酩酊大醉。我不过就是那个先锋,习惯回忆前世之妾,又善于幻想今生之王的那个装逼犯;原来,我不是我,你却还是那个较真、偏执,而又毁人情绪的小混蛋;原来,我的禁忌,不是提笔写字,而是用一碗白水,稀释了夜游的漫长苦旅。
还好,我一直喜欢寺庙、焚香,还有僧侣。
袅袅腾起的烟雾,若果真中和了字字句句里的妖气,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还是蛰伏起来,以狐之魅,过家家,也躲猫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