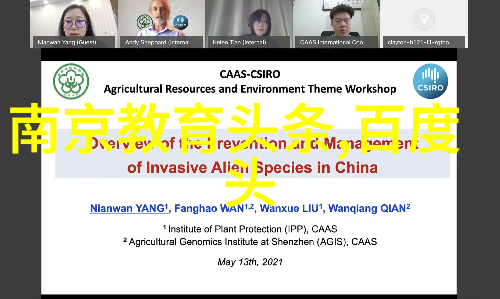花样年华 东方美的浪漫写意 留白与无限的想象空间(花样年华是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作品)
文/刘嘉鑫 《花样年华》是一部极具王家卫导演个人特色又兼具极高艺术水准的电影作品,由于“前人之述备矣”,故在此,我将着重从全局出发,结合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来分析这部电影。 该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后,开始互相接触,并且二人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据了解,电影《花样年华》的灵感来自刘以鬯的小说《对倒》。 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充斥着“错位感”。“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对倒双连是邮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常常邮票的印制都是相同的朝向,而对倒双连是指邮票上下或者左右朝向相反,这就是对倒印刷形成的,这种不太常见的情况也和电影中纠葛的人物感情线暗合,苏丽珍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妻子有了一段婚外情,二人发现之后,也随之越走越近,产生了感情,这就像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在错位的感情中诉说着一段暧昧又不能宣之于口的故事。 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有着不谋而合的联系的,是电影里苏、周二人的感情,满是遗憾和错过,是那句没说出口的“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是苏丽珍来到新加坡时的故意隐瞒,是那通响了三秒但在接通后却沉默的电话,是周慕云再回到香港时没敲响的门…… 这一切就像是对倒的双连票,充满着“错位感”,但又不得不承认,或许这就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隐晦的爱慕通常和暧昧、混乱、匆忙、隐蔽…… 这些词联系在一起,错位的遗憾又在曾小心翼翼避开邻居的行为中被放大,而二人感情的结局又将这种小心翼翼的相处和不能在一起的现实推向极致的矛盾,同时也体现出了含蓄婉转的东方美学,意犹未尽,不胜感慨。 这种东方美学,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克制”,特别是电影中苏丽珍的“旗袍”暗含着色彩叙事的手法,将“克制”的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家卫在采访中曾谈到,旗袍就像苏丽珍的心情,在整部电影中旗袍也能作为一种时间标志,因为在电影的叙事中不能够像新闻一样,明确地写下几年几月几日,更多的是用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日月星辰…… 这种意象来传达时间的变换,而《花样年华》的主要拍摄场地是室内,因此苏丽珍旗袍的更换也是我们明确时间变换的重要线索。 而谈及“克制”,张曼玉在访谈中也有说到,旗袍是根据她身材订做的,反复改了很多次,就是为了达到最贴身的效果,所以在穿着旗袍拍戏的时候行动非常受限制,也不能做大动作,在我看来这种“束缚”。 首先是一种行为的克制,让苏丽珍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是陈太太,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守妇道,而另一方面是对情感的束缚,要时刻克制自己对周慕云的感情,这种感情的克制其实并不是单方面的,周慕云对苏丽珍亦如此。 他来到柬埔寨的神庙,对着一个洞口诉说着自己的秘密,说完以后他用杂草堵上了那个洞,这与他之前所说的古时候的人诉说秘密的方式不谋而合,他诉诸的或许是对苏丽珍的爱慕之情,即使两个人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是周慕云在寻找那双绣花鞋时的着急。 苏丽珍在孙太太提起往事时看向窗外的湿润的眼眶,或许都能说明些什么,电影的黑色字卡对于这种缱绻缠绵的刻画有切中肯綮的效果,“那些消逝了的歲月,仿佛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沖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而“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那是一种带有宿命感的注定。 刚刚提到“怀念”,其实片中的配乐插曲和两种方言的交织也能体现导演的这种怀念,对过去的人、事、物,包括那时候的生活方式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 片中的插曲除了反复出现的三首配乐外还加入了很多戏曲,其中《红娘会张生》一曲虽是粤剧,但原作却是荀派京剧的经典,而孙太太连同家里保姆讲的上海话与周边的粤语环境形成了一种神奇的融洽感,而苏丽珍作为上海人几乎都讲粤语,但在和孙太太的对话中会不时流露出几句上海话,又是一种矛盾的融合,让人觉得上海话和粤语在同一个场景下出现并不奇怪,甚至有些理所应当的自然,这也是导演的个人经历所造就的。 王家卫出生于上海,五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他对上海有着特别的情愫,因此他的电影中也处处有着上海的影子,他乐于也善于去记录那个年代的特殊风情,港风和小布尔乔亚交织,正是最具魅力的写照,他用瑰丽的笔触写下一首沪港情诗,让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八音盒永远鸣唱。 《花样年华》是一场对倒克制的感情戏幕,它没有一个引导性的尾声,更多的是一种停留,对一个时代的短暂回眸,让那抹上世纪的风情永远刻在胶片上,让那段遗憾的诗歌不再有终章,让一切随风。